来源:党委宣传部,文学院 | 点击量:发布:2024/06/27
供稿审核:黄江滔,左兴才|
编辑:孙红梅|
编审:黄江滔
张瑞英,文学博士,澳门百家家乐(中国)官方网站,二级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。山东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,山东莫言研究会副会长,山东茅盾研究会副会长。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,在地域文化与乡土小说研究、文化视域中的现代小城镇小说研究,以及张爱玲、萧红、莫言、余华等作家研究方面较为用心。近几年在《文学评论》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《文史哲》《鲁迅研究月刊》《山东大学学报》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,部分篇目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、摘要。已出版《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》《文化视阈内小城小说研究》等专著。主持完成国家、教育部及省社科项目及研究生创新项目多项,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、二等奖等奖项。

我走近文学,源于高考志愿填报时的懵懂爱好,走进文学则基于多年后的理性认知。文学是写人化人养人的,任何一部经典,都是一个伟大灵魂的人生轨迹,它们给出了在面对人生重要命题时的态度与选择,对读者的启迪、引导是全方位的。研究文学,是在一定的学术规范内与作者的灵魂对话,懂和愿意去懂是对话的前提。鲁迅谈及《儒林外史》时说“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……伟大也要有人懂。”只有真正懂生活,懂他人,而且愿意试着去理解、会意,才有可能真正懂得对方的故事和意图,意识到对方的别有用心或别具只眼,在此基础上,才能有真正的交流与批评。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让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对话、交流的重要性,也在写作、研究甚至包括生活中,逐渐拥有了这份用心和耐心。

作为一名文学评论者,我经常关注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,双方理解的错位、观点的不服,是经常出现的现象,究其原因,在于创作与批评两种理路的各有机杼。就文学创作的起源而言,劳动说、模仿说、游戏说都不同程度地源于外在需要,而经典的伟大恰在于其灵魂轨迹之独特,于他们而言,文学就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手段,如何能精准、自如地传达自我是其目的,这类写作往往并不在意文学的固有规范和传统的各种条框,写我、传我、达我才是最终目的。莫言曾不止一次地强调,创作源于饥饿和孤独,而其“真正的写作动机”是“想用小说的方式,表达我内心深处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想法”。正是认识到这一点,我的学术研究从过去注重循规蹈矩的专业规范,走向追求与作家作品的心灵沟通,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的文章《一个“炮孩子”的“世说新语”——论莫言〈四十一炮〉的荒诞叙事与欲望阐释》正是这种认知的践行。国家课题的结题成果,著作《文化视阈下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研究》也是这样思考和践行的。既然优秀的作家是用生命写作,研究者自然该与其以生命对话。

作为文学研究者、批评者,我时时警醒自己,一是不要被文学创作的表面现象或局部现象迷惑,忽视了作者要表现的根本原因和最终目的;二是对作家或作品思想、艺术本身要予以充分尊重,不要想当然地替他人做主张。看起来问题似乎并不复杂,但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,真正做到透过作家所表现的对象,理解作品的皱褶纹理,懂得作家衷肠心曲的人并不容易。借某种现象、某部作品找个基点自说自话,将文学批评变成展示自我知识和理论的机会,这样的研究容易,但是走不远。因为其一,不尊重他人辛苦的创作成果,其二不尊重自己本真的感觉和思考,其三对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工作缺少职业性尊重。这种种不尊重的背后其实是缺乏对职业真诚的敬和对人生执着的爱。有了这种真诚的敬和深沉的爱,才会有对世界万物理解包容的大气和对抗世俗、反抗绝望的勇气,才能真正愿意去懂具有同样情怀的作家、作品。我时时提醒自己,无论做人、做学问,永远保持这样一份“敬”与“爱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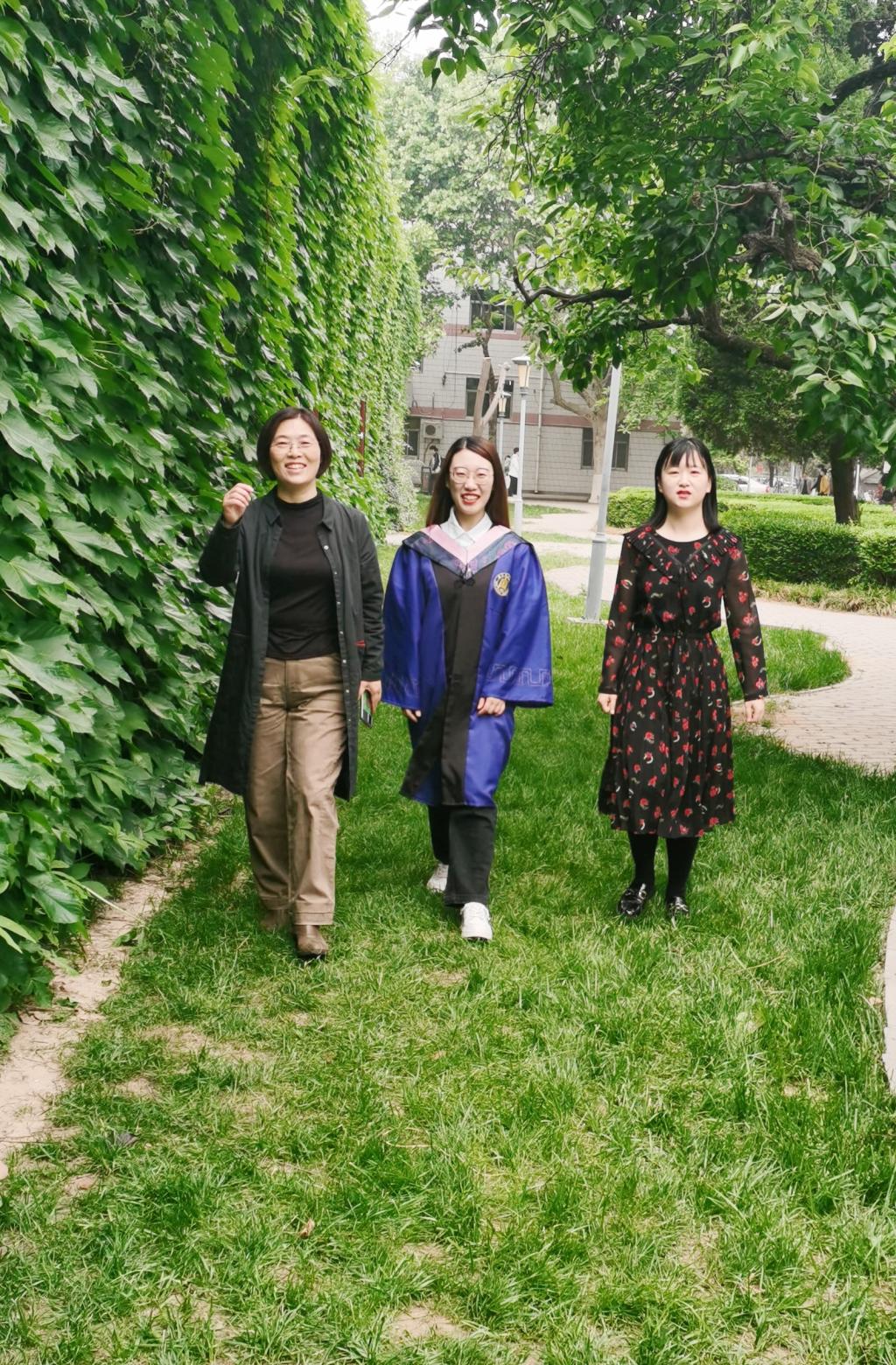
与上述相关的是我作为研究者身份定位的认知。就作家创作而言,无论是传统的“诗教”思想,还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“启蒙”观念,目的都是“以风化下”,作者是居高临下的精英位置。莫言的“作为老百姓写作”,不仅仅是一种态度,也是认识世界、理解人生的一个视角。作为文学研究者,自然也应该对作品在理解、共情的基础上与作者“感同身受”。从某种意义上看,这样的视角会去除因地位、知识、修养、经历等种种差异所带来的对世事人情认识上的遮蔽,将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视同自己,感受它们的情感世界、理想追求、价值意义。这样的研究是有生命的,因为生命体验的“真”,更容易抵达思想感悟的“深”。
近四十年的文学研究让我认识到: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懂与愿意懂的知音解读、评析,相当的思想、境界、追求以及懂和愿意懂的愿望旨趣,让研究者不仅懂得作者的题中之义,还能别有会心地理解其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。如果只是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理论、规范去评判作家、作品,则无异于削他人之足适自己之履,是万不足取的。作为评论家应该懂得,真正的好语言是得体,真正的好结构是浑成,一旦拿各种条框这把手术刀去剖析,那必定是一地零碎。没有灵魂的技巧没有意义。